坐在剧烈抖动的机器旁,我将电话接在耳边。机身的震动像胸腔里的鼓点,金属外壳持续发出喀嚓、喀嚓的声响,墙角的线缆随节拍轻轻颤动。空氛里滚动着一股刺痛的电流,空气像被拧紧的绳索。我要说清楚的事情在喉间打结,话筒里传来不稳的回声,像有人在另一端摸索着话题的边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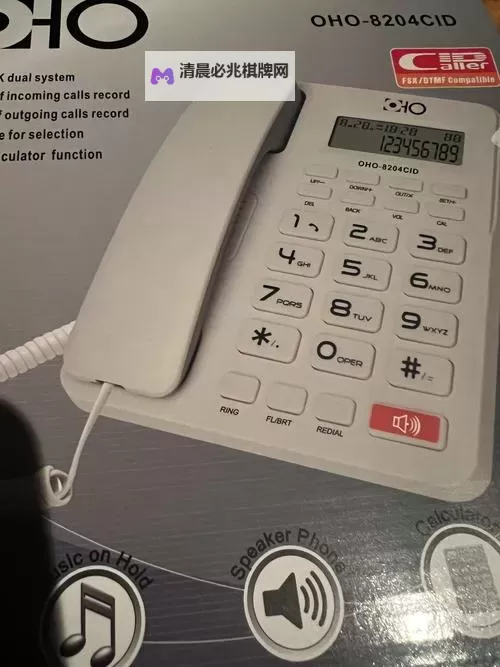
声波穿过噪声,像一支被火花拌乱的笔,划出一道道模糊的线条。回声并非简单重复,而是在对话的边界上不断推移。声音在空旷处折返,带来熟悉也带来陌生,像老友的问候混入潮汐的泡沫。对方的声音变得含混,词语被震动的空气分离,再次回到胸腔,成为需要辨认的碎片,宛如夜里落下的雨点。
我在这场声学的风暴里寻找清晰,像站在风口处标记一条线。每一个顿音、每一次停顿,都像在地表刻下记号,记录是谁在说话,谁在倾听。噪声不断侵入,边界却在我和对话之间慢慢显现:若把话讲清,信息会流失;若留一点空白,误解却会在心里落下种子。
写作里常有这样的时刻,文字像舞者在无声的空间里练习呼吸。这里,电话成了笔筒,话语成了墨水。我把颤抖里的句子取出,拼合成一条看得见的线,让对话的意义在静默里停驻,哪怕只是短短的一段。回声像潮水退去后露出的海床,清晰处留痕,混沌处只剩消散的痕迹,像遗落在地板的贝壳,稍纵即逝。
通话结束,机器仍在颤抖,房间回到初始的静默。边界没有消失,只是在新的噪音里被重新划分。我忽然明白,这些被打断的声音其实在提醒我,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常常跨越不稳的媒介,穿过干扰,抵达彼此的心脏。也许回声并非要完全返回,而是把原本的距离拉近成可感知的一条线。
